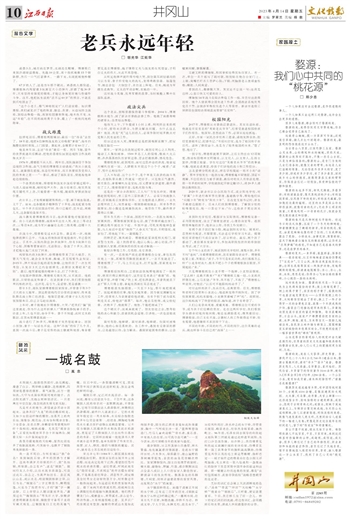□ 胤忠
水面阔大,船舫悠然前行,浪花溅起,漫漶了白云。两岸峰峦藏卧,连绵拥翠,四周皆是墨绿的倒影。雾气渐散,远方一碧如洗,天空与水面似两面对视的镜子。点点阳光洒下,光线在树林里浮沉。一只老鹰在半空盘旋,倏忽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凡是有水的地方,表情就会灵动丰富起来。这条名曰“九龙”的湖泊酷似蛟龙,又如少女扭动纤细的腰肢,坐落其上的欢乐岛、情缘谷、桃花岛、长寿谷和观音吉象、少女思春、长老点赞、金蟾望母等景观如纤纤十指相扣,相映成趣。尤其是“观音吉象”,正看犹如观音双手合十祈福祷告,侧看又似一头巨象闲庭信步。
典型丹霞地貌的天柱峰,显然比别处多了些眼波流转、巧笑倩兮,也掀开了铜鼓秀美颜值的一角。
我一直不明白,为何有城以“鼓”命名?来到铜鼓石旁,多年的困惑方才解开。这块布满岁月印痕的巨石,因“色如铜,形似鼓,击之有声”,遂名“铜鼓”。据同行友人介绍,以往水流丰沛湍急,可没过此石,浪击之,当真声如丝乐。县区或以山名,或以水名,唯独铜鼓标新立异,以石为名。“铜皷石”三字正楷竖书,鲜明俊逸,只是为了简便书写,才将“皷”字一撇去除。石上存留古人题词篆刻多处,“潘周过化”“题铜鼓石”等朱红大字,依稀讲述着明朝著名将领、铜鼓营守备邓子龙将军剿灭叛乱、让铜鼓复归王化的英雄气概。巨石中间,一条裂缝清晰可见,那是西晋年间许旌阳在此追斩蛟龙、放出金鸡的鲜明印迹。
铜鼓石旁,定江河水流淙淙。每一条河流,都有它的前世今生。千百年来,这条铜鼓人民的母亲河一直默默流淌,不事张扬,它将万顷碧波送入清清修河,奔腾倾注浩渺鄱湖,最终归入滚滚长江。它的水质常年稳定在一类水标准,水质综合指数连续多年位居全省第一,娃娃鱼、棘胸蛙等濒危水生重点保护动物在此栖息繁殖。它不仅为铜鼓人民提供饮水和洗菜浣衣的源流,更见证了无数铜鼓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身影。它同样注视着一批批读书人背井离乡追寻梦想,也率先陪伴了外来官员、商贾、匠人、移民、僧侣与铜鼓的邂逅。其中,就有名士苏东坡的羽扇纶巾。
宋元丰七年(1084年),朝廷调东坡赴河南临汝任职。接到圣旨的东坡并未立刻启程,而是决定先南下江西,看望担任笃州税吏的弟弟苏辙。途经带溪,听闻此地有位“隐居乐道、不求闻达”的布衣儒生胡安鼎,于是慕名前往拜会。消息传开,胡安鼎及全村男女老幼皆欣喜万分,村里像过年一般热闹起来,为远道而来的贵客接风洗尘。接下来两天的带溪光阴,将被两位名士满腹经纶的碰撞与激荡填满。他们携手攀龙门山,观磨盘石,赏带溪水,谈古论今,吟诗作曲,大有相逢恨晚之意。见多识广的东坡没有想到,偏僻的带溪山水竟如此绚丽多姿,陌生的江西老表竟如此热情豪放,胸中一气呵成长诗一首。“篮舆暂憩诣造门,竹马儿童欢迎候”“带水清,泉石透。中有高人自在居,耳可洗兮齿可漱”……至今读来,仍可领略当年的美景与盛况。
漫步铜鼓,目之所及皆山峦叠翠、林木繁盛,处处氤氲着诗情画意。走进永宁镇坪田村,古木参天、绿荫蔽日,漫山遍野的茶树嫩芽摇曳,金黄的油菜花田鳞次栉比。客家博物馆内,馆主四处搜罗的窗棂、樟木箱、储物柜、牌匾、竹器,都在默默诉说占全县八成以上人口的客家人勤俭持家、耕读奋斗的优良传统。散落各处的吊脚楼、古祠堂,同样洋溢着浓郁的客家风情,高度契合“永宁”的寓意。
永宁镇因桥得名。始建于清雍正年间的永宁桥,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铜鼓重修永宁石桥记》明确记载:“一廛两市间,往来日凡千百辈,奔腾浩瀚,非桥不为功。桥成义举,宁人宁国,永捶无朽,故名永宁。”历经风吹雨打、洪水冲击的永宁桥,尽管青石斑驳,略显老态,但依然身板紧凑,巍然屹立。96年前,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第三团就是通过此桥进军浏阳,攻打白沙首战告捷。站在桥上,我仿佛看见秋收起义波澜壮阔的史诗场景,仿佛看见第一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高高飘扬,仿佛看见风华正茂的毛主席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刚才徜徉过的燈星台红色公园又浮现脑海,毛主席在一张八仙桌和一盏煤油灯的陪伴下苦思冥想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出路。那一幢幢古朴而沧桑的房屋,都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战略思想萌芽的见证者。
美好的词汇总会被上天泼洒鲜亮的色彩。“汤里”“带溪”“坪田”“天柱峰”“永宁桥”“燈星台”“铜鼓石”,只听着,便觉浓墨重彩。午后,我在桥头坐了好一会儿。桥下的定江河汩汩流淌,将这些词汇,会同鹅卵石和水草,谱成人世间最曼妙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