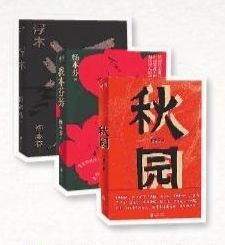□ 周 颖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滇敏 实习生 张一朵
江西铜鼓人杨本芬60岁开始她的厨房写作,2020年出版的小说《秋园》成了畅销书,这本书写两代普通中国女性生命经验的小书,先在读者中受到认可,继而获得第六届谷雨文学奖等奖项。《秋园》和此后陆续出版的《浮木》《我本芬芳》,被媒体称为“女性三部曲”。她坚持写作的动力在哪,她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年过八旬的她还在写吗……记者带着很多疑问,敲开了杨本芬的家门——
文学是人学,是镜与灯,读者在这里映照自身,又在这里触摸生命。杨本芬的创作小而沉,是细腻的生命歌哭,满是肉搏的痛感和真情。并非只有海洋才值得书写,溪流也自有它的澎湃和迷人。
想写而写
六十来岁,在南京带外孙女的杨本芬开始尝试一件从未干过的事:写作。创作在一间四平方米、褒着热汤的厨房里进行,高凳为桌,矮凳为椅。创作的初衷是为了写出她母亲——小说中的秋园——的一生,她是当回忆录来写的。
完稿后,书稿在女儿章红手中好几年,没有出版的机会。2009年,章红开始在天涯论坛“闲闲书话”栏目更新妈妈的文章。开始,有论坛的网友留言说,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人愿意看。渐渐地,认同的声音多了起来。画家虫虫在下面跟帖,“底层叙述的声音很珍贵”,也是虫虫牵线,促成了乐府创始人涂志刚与《秋园》的出版合作。
彼时,南昌人涂志刚的品牌尚在草创期,只出版过几本书。之后他签下了杨本芬这个无人知晓的素人作者,首印数为5000册。章红介绍道:“涂志刚认为《秋园》有可能卖20万册。这个判断成真了,两年时间,《秋园》已经卖到25万册,销售数字还在增长。”出版人涂志刚不认为“杨奶奶”是素人作者:“我本质上是签下了一个作家的书,只是这个作家从前没出过书。”这是一个出版人和写作者相互成全的故事。
一本畅销25万册的小书,把这个在四平方米厨房里写作的老人推进了“女性作家”的行列。《秋园》先后获得豆瓣2020年度中国文学(小说类)第二名、第六届谷雨文学奖等12项奖项。
《秋园》书写母亲,《浮木》让一家人在纸上团聚,《我本芬芳》勇敢地刀刃向内,书写婚姻。如果说,最初的写作是对母亲在这世间痕迹近乎本能的捕捉,那么她后来的写作则属于有意识地从个人延展向社会,去触碰乡间普通人的生活,继之又从个体生存经验转向婚姻生活本质这一纵深。《我本芬芳》有着欧亨利式的辛辣结尾:“她终于知道,这六十年的婚姻——大家眼中的钻石婚——的确也是固若金汤的婚姻,只有她和他没能获得幸福。她有她的伤痛,他有他的伤痛……他们本该相爱的。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从第一篇在文学期刊发表的短篇小说《乡间生死》,到今天的《秋园》《浮木》《我本芬芳》,杨本芬真诚细腻的写作在万千读者中激起回响。她自己依然无法坦然面对“作家”这个称谓。“我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采访中,她笑容里的羞涩闪过,“我怎么就是作家了呢?”
相识多年,涂志刚眼里的杨本芬“淳朴,有天真之气,并且这种天真之气会透过她的文本传达出来”。
太想读书了
83岁的杨本芬还记得自己17岁离家外出求学那一天。100里的山路,母亲送了10多里,一直送到白山坳,站在山坡上一棵松树下对自己不住地招手。
裹过脚的母亲几乎咬碎了牙,将二女儿杨本芬送进了学校,但求学梦却终是落了空。在岳阳工业学校,杨本芬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吃苦、肯学、每个学年拿头名。三年后,学校停办,杨本芬茫然四顾。
只身抵达宜春火车站时,她身上只剩一角六分钱,花八分钱给妈妈和弟弟写了信,八分钱买了碗糯米稀饭。到底是蹦蹦跳跳的年轻女孩,带着股初生牛犊的憨劲儿,一脸无畏地扎进了衣食无着的生活。
她还是想读书。打听到当地有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她立刻跑去。招生时间已过,在她的极力恳求下,老师考核了她,并告知在这里念书可要吃得了苦。她连连点头,只要能上学,吃苦算什么!她选了师范班,美滋滋地计划着毕业以后可以当个老师,挣钱帮妈妈养家。然而,一年后,她无奈地下放农村。
遇到章医生,这段一见钟情的仓促婚姻改变了她一生的行路轨迹。但即便是20岁无奈嫁人、赌气般剪掉两条油亮的齐腰大辫子的那一刻,她对丈夫的要求依然有这么一条:送自己去读书。
“我太想读书了呀,一辈子都想读书,没机会啊。”因为做了妈妈,杨本芬的读书梦就此终结。此后,她在灶台、孩子、生计间奔走逾半世纪,直到2020年6月《秋园》出版。
她的身上保留着人性的丰富、真诚、温厚与冲突。她在自己的婚姻里奔走63年,从不讳言婚姻的遗憾,也不止一次地告诉周围人:“爷爷没看过我写的《秋园》噢,给他看他也不要看”,但爱并未停歇。“读者们都说老章是‘渣男’,可怎么会呢?他是一个好医生、好爸爸……”女儿章红记得,爸爸离世时,妈妈不停地亲吻爸爸的额头,“我们甚至担心她会被感染”。
她把无法展平的遗憾和生活的钝痛,写进了书里。
母女
“你怎么不能是作家呢!当一个人为自己而写,写作就开始了,她就是一个作家。何况现在你都出版了三本书呢。”女儿章红是出版人和儿童文学作家,她是杨本芬的精神对话者,也是她作品的第一读者和第一编辑。
她的主卧里有张小沙发,紧挨着床。“每次回家,我就坐在小沙发里,妈妈斜倚在床边,我们就一直聊天。”章红说,“妈妈总爱说‘我们来说下话’。”这个生活场景出现了太多次,以至于章红离开南昌回到常居地南京时,杨本芬在电话中说:“我有时候看见沙发,还是会觉得你坐在那儿,跟我说话。”
章红说,每次离开南昌都是一个“关卡”。回程的路需要穿过小区大型露天体育场。杨本芬腿不好,但必定坚持送到体育场门口。章红走在空旷的体育场里,走几步便一回头,跟妈妈挥一挥手,到后面其实已几乎看不清妈妈的身影,也还是对着那个方向挥手,直至转弯,不可能再看见彼此,“我知道她一定在那儿。”章红说,“我知道她依依不舍,但我还是得离开,我总归要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啊。”
在写作上,杨本芬说:“我女儿那关太难过了!她太严厉了,我要写得很好了才会给她看。”
“女儿是母亲最严苛的批评者。”章红说,她知道妈妈非常了不起,但还是会对她心存批评,“我身上有妈妈的影子,当我在她身上看到我一直想要克服的东西,就会审视她,想要改变她。我想这是我的问题。真正的爱是不要求改变对方的,何况妈妈成长的时代与我完全不一样……”
路口
春日的南昌,阳光渐暖,穿堂煦风里,一只遛弯的小狗脱缰般穿过楼栋。杨本芬南昌的居所,就在这座安静的大院里。穿过走廊上楼,鸟鸣声、狗吠声、老人谈天的细碎声,一并被关在了屋外。几间房门都静悄悄地开着,偶尔有快递员敲门,地板上清晰传来白狗毛毛有节奏的打呼声。南向有日光洒进窗台,北向的屋子里,洁净的蓝色床单铺在那儿。“爷爷走了,我一下子走不出来。我们开着门,觉得他好像一直都还在那。”
“爷爷”章医生今年初离开,这是她人生的另一个路口。至此,时间、生死皆坦荡。
家人眼里,特别爱笑的她不太笑了。“妈妈、哥哥、老章都走了,我在这世间还能有多少欲求念想呢?”她熟稔地取来不远处章医生的照片,五六寸大小,镶嵌在洁净的木头相框中,一尘不染。
她爱美了一辈子,如今每每看到镜中迟暮的自己,会忍不住给自己做心理暗示:“83……我83岁了,丑是应该的。”她念着数字的可爱模样让在场的年轻女孩笑出声来。
需要抵抗的,还有衰老和时间。身体的不自由限制着书写,她的左眼做了白内障手术,双腿膝盖术后恢复慢,无法久坐,每日伏案不能超过3小时。于是只好分时间段写作,上午、下午、晚上分开写。她在书桌上打开平板电脑,坐着写会儿,沙发上仰着写会儿,靠在床上写会儿。
写作成了生活里的光亮。“我写三部曲,当时只是因为喜欢写,现在回过头看,觉得值得写。”如今,第四本书早已交稿,年内将出版。她已经为第五本书伏案了两三个月,这是一本婚姻主题的书,灵感来自小区68岁的女邻居。杨本芬说,从前写得快,一气呵成,而手头在写的故事,慢,总也不满意,常感笔头阻塞,“我怎么处理人物的下流话呢?那真的太脏啦。”这是她当下写作中直接的苦恼。在涂志刚看来,杨本芬在最近三年的创作里完成了从自发写作到自觉写作的转变,“她开始表达其他女性身上的‘勇’,书写在她面前打开的世界,这是职业作家的工作方式。”
杨本芬83岁了,没有放下笔,溪流的澎湃自有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