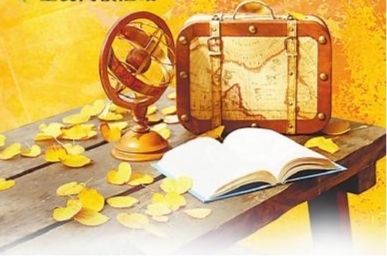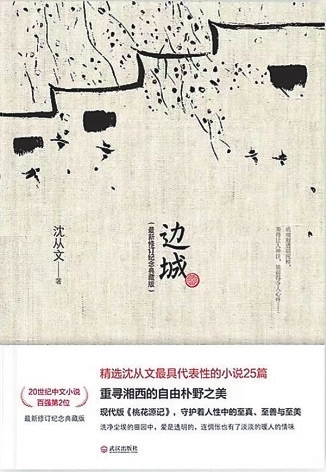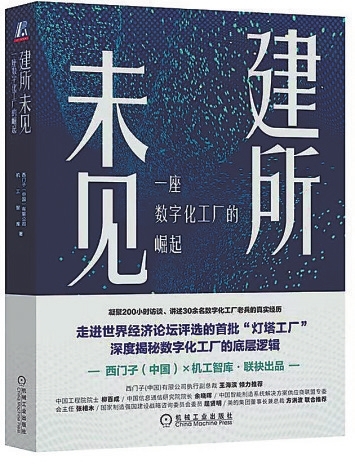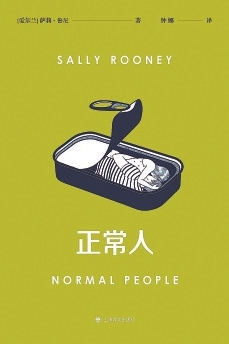编者按:对于爱书的人来说,世界读书日只是他们长久读书日常中的寻常“一瞬”。我们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来谈谈他们的读书“一瞬”,与大家共同分享这一室书香。
《边城》不遥远常在身边
□ 张品成
想想,我书桌上摆放最久的一本书是沈从文的《边城》。
最早读到这本书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考入了江西师范大学,在图书馆偶然借到一本叫《边城》的小说,是20世纪40年代的版本,繁体字竖版,印象中是当年上海一家书店印制。我当年就学的大学中文系,其前身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文系。这些书,就是当年留存下来的,书的封面赫然印有硬币大小蓝色的章,“国立中正大学图书馆”。我们入学那会,一切还没走向正轨,书店还没有《边城》,我此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沈从文的名字。但这本不长的小说,当时就让我惊诧,随之让我入迷。
后来,那本书出版了,我第一时间到书店买来新书,再后来,我搜来许多版本,即使到湘西等地旅行,也要购来这本书存留。其实有一本也就足够,但我觉得有新版本,为之重读,肯定有新的感情和收获。
我是那么坚信,其实也确确实实是那么回事。
《边城》并不是那种故事引人入胜的小说,平实的文字,平实的人物,平实的情节,一切平平实实,却真正地引人入胜。不仅引人入胜,是将那些美丽在漫不经心中展现。平缓朴实中,充满了一种无以言说的力量,有着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小说的情节简单而又简单,山城茶峒,山清水秀,美不胜收。故事从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朦胧爱情切入。青山绿水,码头和船……年迈的艄公和他十六岁的孙女翠翠,河水缓缓地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的傩送……《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老艄公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
好多年了,我一直咀嚼。我用“咀嚼”一点没有错。《边城》里每一个字,我曾经饶有兴味地“咀嚼”,也常常让我思考,一部薄薄的小说,竟然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大师沈从文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自己后来成了写作者,我跟很多人谈到学习写作。一些人习惯于向大师致敬(影视界尤甚),说的是学习模仿,但这种“致敬”不能一直伴随你,我是很清楚这一点的。说实在的,我的写作的成长,真的得益于《边城》很多。
先是语言。我当年十分诧异,很平实的语言,怎么这么耐读?研究知道,作品在普通的语言中间夹有湘西少数民族的语言,节奏虽然缓慢,但很切合边远淳朴的风情,淳朴的人物,淳朴的生活和民风,淳朴的爱情和故事……
汪曾祺是得了他老师沈从文的真传的,当然,湖南的一批作家,还有陕西的贾平凹、杨争光等,也是领悟其语言之精妙从中学得很多。从那时起,我处理特殊的地域、特殊的人物,必须结合当地的特殊语言予以表现。所以,加以改造的客家方言,成了我小说语言的韵味,也特别契合赣南闽西的独特风情和人物(中央红军士兵大多是客家人)。
避免大众化写作,避免同质化内容,给读者提供非常态阅读,也是我在“咀嚼”《边城》中悟到的。我写的多是江西红色历史题材,写的是红军,最容易落入俗套,我在这方面格外小心。先是别人写过的坚决不写,二是人物塑造和故事的设置,都要打破常规。当然,一切遵循正能量原则,表现真善美,表现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的精神品质这个原则不能丢。
直到现在,《边城》依然是我案头常备并常读的一本书,这里我推荐给大家,没读的一定读读,读过的不妨再读几遍,一定收获多多。
散发着幽蓝的光泽
□ 王 芸
蓝色印章,呈一本摊开的书的形状,中间嵌有两行字“综艺图书社 创造精神生活新境界”,旁边盖有我早年的名章。它们躺在《茨威格小说全集》三卷本每一卷的扉页。书的外封已有破损,内页纸张泛黄,排列紧密的细小字体不太方便阅读,可这套1997年在家乡小书店买到的书,一直跟随着我,经历多次搬家,从家乡来到异乡。20多年来,我的阅读视域不断拓展,读过许多经典之作、精彩篇章,也创作了数十篇小说,可对茨威格作品的喜爱没有在时光绵延中削减一分一毫。
这套书是1995年出版的,由高中甫主编。茨威格的书在国内衍生出众多版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小说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精选集,也有不少单行本,《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昨日的世界》《良心对抗暴力》……
初识茨威格,在大学图书馆。那是30多年前,茨威格从绵密的文字间伸来的“一双手”紧紧抓住了我。那是一双远离并背叛了理性与信仰的手,一双陷在疯狂的欲望之涡中无力自拔的手,最初读到《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关于那双手的段落时,让我惊异。大学校门前有条笔直的小路,路边有家书店,在那里我买过茨威格的几本书,然后在家乡遇到这套《茨威格小说全集》,毫不犹豫买下来。
《心灵的焦灼》《象棋的故事》《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生命的奇迹》《人类群星闪耀时》……我在茨威格的文字里,一次次读到火焰的形态,火焰燃烧时的炽烈,还有最终化作灰烬的叹息,读来令我难忘。曾写下散文《从几个暖色词语朝向茨威格》,我从“手”“火焰”“故乡”“战争”“蓝色”几个词语出发,写下关于茨威格的阅读感受。“学过哲学的茨威格通过火焰,和被火焰烧灼的生命形态,表达着自己对命运、对生命的理解。在他看来,火焰存在于每一个生命内部,只等偶然的外力到来……”茨威格作品对我的影响,对我小说创作的影响,要等到很多年后才会清晰浮现。
悲天悯人的天性,决定了茨威格的生命选择和抗拒方式。当命运已经尘埃落定,世人知道了这个经历过一战和二战,经历过自己的作品被投进火堆焚毁,经历过恐吓、迫害、辱骂,不得不离开家乡奥地利四处流亡的人,最后在巴西与这个世界主动告别,“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敬!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还能见到朝霞!而我,一个格外焦灼难耐的人先他们而去了”。
悲天悯人的天性,也决定了茨威格的作品质地。茨威格曾借书中人物的口这么说过,“一个人,应当有这样一双眼睛,蓝汪汪的,光彩照人,饱含着一种内在的虔诚”。在他的诸多小说中,我能看见一双眼睛,晶莹如水的蓝色,温柔地,悲悯地,注视着这个世界,注视着在焦灼中奔逃的人、被战争逼迫的人、于命途辗转的人。
“当这个一无所知的盲人那样欣赏一张废纸时,我脊背上不禁感到一阵发冷……真让人难过。”重读茨威格的小说《看不见的收藏》,我联想到卡佛的《大教堂》,一个是酸涩中的明亮,一个是虔诚中的悲伤。那个盲人收藏家,不知道妻子和女儿因生活所迫,在战乱年代物价飞涨的困境中不得不变卖了他收藏的名画——27本画册中,他怀着虔诚、骄傲、欣喜一一展示给“我”的,不过是一张张泛黄的纸,上面空无一物。
让我触动的,不是善意的谎言所揭示的战争残酷,而是一个细节——这个盲人的国籍,他是德国人,他属于一个正在挑起战争的疯狂民族,正是这个民族制造了茨威格和千百万犹太人,乃至更多人的伤痛和苦难。可茨威格还是通过自己的笔,将悲悯洒布于他的身上,因为他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被侵犯者。他的不幸,依然令茨威格“背脊上不禁感到一阵发冷”,感到“难过”。在茨威格那里,有对每一个微小生命的关注,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和对战争、暴力的谴责。
“我害怕人类相互残杀的战争更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昨日的世界》),这句话足以解释他最后的选择。身为犹太人,他被迫流亡,成为战争直接威胁、侵害、侮辱的群体之一。因为“无根”,他才把世界当作自己的家乡,把人类命运与自身命运执拗地牵绊在一起。一种广泛而深情的人道主义,深深植根在他的灵魂深处。
茨威格说:“一个喜欢自由而独立阅读的人,是最难被征服的,这才是阅读的真正意义——精神自治。”阅读是一种自我精神教化。经由书,我们走向无数分岔的大道小径,帮我们建立起基本观念,包括世界观、自然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让我们确立自己的生活原则、行为边界与生命选择。茨威格,这个“最难被征服的”人,以他满布悲悯的作品,书写着一颗颗柔弱而坚强心灵的絮语,书写着人类灵魂深处的痛苦与幸福,他那些“在地球所有语言中找到了友谊和接受的作品”,散发着深远的、幽蓝的光泽。
中国制造的数字化“灯塔”
□ 李玉亮
数字化时代已然到来,数字化与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正以切实价值和巨大成就成为传统制造业向更广阔领域创新转型的重要引擎,中国也在技术变革浪潮下开始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和智能制造工程。
《建所未见:一座数字化工厂的崛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智能制造的理论性著作或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性参考书,而是一本来自西门子工业自动产品成都公司(以下简称西门子成都工厂)一线,非常具有实践性和故事性的书。本书再现了2010年以来西门子成都工厂的崛起历程,以关键人物的视角,复盘了在面临重重挑战时,这座数字化工厂如何以非凡的变革毅力,实现了从0到1再到100的领先发展过程。作为中国“工业4. 0”示范工厂,它在2018年被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为首批9个“灯塔工厂”之一。
从复刻西门子德国工厂到本地化独立经营,从引进消化吸收德国理念到自主数字化创新,从面向本地研发到面向全球研发,西门子成都工厂不断探索和突破为中国企业如何从零开始打造数字化工厂,如何通过持续变革实现数字化持续领先给出了清晰而令人信服的答案。本书首先梳理了这座工厂在谋划、建设、巩固与进化四个时期面临的挑战和应对,其次重点总结了经典项目、对外赋能和数字化技术领域探索案例,深入方法论层面,从战略、创新、企业文化、人才角度剖析了西门子成都工厂成为数字化灯塔的底层逻辑。把一座现代化数字工厂的规划建设、组建团队、生产运营、管理运营、数字化技术应用、流程精益、质量管控、产品研发、企业文化和组织变革全面展现给读者。
总之,这是一本值得品味的制造业“故事书”,可以给产业政策制定者、工业制造从业者和企业数字化推动者一些参考。
社交媒体时代的爱情小说
□ 阿 袁
我读书,是有些势利的。
总喜欢读那些名家写的书,名家写的书,就像出身诗礼簪缨之家的公子小姐,一般差不了。即便有的初看起来,这个公子可能是“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的宝玉,以为自己这一回上当了,然而只要耐心读下去,读到后面,就会发现,这个“草莽”,原来是可以写“槎牙谁惜诗肩瘦,衣上犹沾佛院苔”的草莽,是可以写“松影一庭唯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的草莽,于是兀自洋洋而笑,再一次觉得自己这种慕名而读的方法英明正确。毕竟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而书又那么多,多到我们不可能用披沙沥金的方式一本一本去读,那是无论如何读不过来的。
所以,如果萨莉·鲁尼不是爱尔兰人,我是不太可能读这位1991年出生的女作家小说的。爱尔兰那是什么地方?虽然它的文艺被乔伊斯嘲弄为“一面仆人的破镜子”,但这面仆人的破镜子,可是不容小觑的——它是叶芝写了《当你老了》的地方,是乔伊斯写了《尤里西斯》的地方,是托宾写《布鲁克林》的地方。我是相信基因的,文化基因应该也和生物基因一样,是有它强大的遗传性的。
如果不是因为那句十分浮夸的评语——“千禧一代第一位伟大的作家”,不但“第一位”,连“伟大”都用上了;如果不是《巴黎评论》把2017年的年度最佳小说颁给了萨莉·鲁尼的《聊天记录》,《巴黎评论》呀,文学殿堂级别的,一向刻薄势利如英国老太太——是《唐顿庄园》里老伯爵夫人那样的厉害主儿;如果不是她的《正常人》入围布克奖。要知道,在我的评价体系里面,布克奖的含金量,可是不在诺贝尔文学奖之下的。总而言之,如果不是这些如果,我是不太可能去读这个才刚刚出道只写了几本小说的萨莉·鲁尼的。
即便如此,我开始读她小说的时候,仍然是满腹狐疑的。“真有那么好吗?”我一边读一边想。这情形,有点儿像一个长相普通的女人审视另一个传说中的美人,不是要看她的好看,而是等着看她的不好看。
康奈尔按了门铃,是玛丽安应的门。她还穿着校服,但把毛衣脱了,只穿着衬衣和短裙,没穿鞋,只穿着腿袜。
哦,你好,他说。
进来吧。
她转身穿过玄关走回去,他把门关上,跟在她身后。走进厨房,几步之外,他母亲洛兰正在褪手上的橡胶手套,玛丽安单脚点地坐上料理台,拿起一罐打开盖的巧克力酱,里头插了把勺子。
这是《正常人》的小说开头。
如果这是一篇我学生交来的作业,我一定会说:你不能这么写的,太啰嗦了,太貌不惊人了。凤头猪肚豹尾,你这个开头,可一点儿也没有凤头的意思,鸡头还差不多——最后那句话,当然是腹说,我是老师,不是刺客,不能用这种侮辱性言语伤害我学生的自尊心和写作兴趣。
但我就是用这种挑剔的眼光看完萨莉·鲁尼的《正常人》《聊天记录》《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三本青春爱情小说的。
看完之后,怎么说呢?我得承认,这几本爱情小说——你也可以把它们叫青春小说,或者成长小说——写得还不错。
它们和经典爱情小说是不同的——不同是比较谨慎的说法,如果不谨慎,是可以用“颠覆”这个词的,它和《红楼梦》语言上的差别,就像锦绣旗袍和粗布牛仔裤的差别;它和《傲慢与偏见》故事上的差别,就像瑞士莲软心巧克力和生姜糖的区别,它和《呼啸山庄》人物关系上的区别,就像城堡和广场的区别。
它们是新爱情小说。
不论是它的写作方式——有人把萨莉·鲁尼称为“细节的原样主义”,但她的细节描写,不是亨利·詹姆斯和川端康成那种带有心理意味和情感意味的古典细节描写,而是漫不经心的,很敷衍的现代人的那种写法。虽然写得事无巨细,却没让读者觉出它的必要性,这从《正常人》的开头就能看出来,人物的每一个细小动作,哪怕是洛兰脱手套的动作,还有手套的橡胶材质,萨莉·鲁尼都没有放过,犹如一个长镜头,这也是为什么它们都被BBC拍成了电视剧的原因,几乎不用改编,原著就可以直接当剧本用呢。
还是谈恋爱的方式——小说里恋爱的发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社交媒体,《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里的作家艾丽丝,是在Tinder上认识仓库工人弗利克斯的;《聊天记录》里的弗朗西丝是用电邮短信和尼克谈恋爱的,并且在得知尼克和妻子梅莉莎有了床笫之欢后,立马用社交软件约陌生男人来报复尼克。可以说,社交媒体是萨莉·鲁尼笔下人物的恋爱日常。
还有恋爱关系的现代多元性——《聊天记录》里的四角恋爱关系,如此混乱又如此严肃认真,用她的“细节的原样主义”方式写,她不评判人物,也不帮人物辩护,这和传统的写法是不同的,托尔斯泰和福楼拜是没有办法让婚外情获得一种道德正义的,所以他们只能让安娜和包法利夫人去死。但萨莉·鲁尼却让弗朗西丝和尼克的妻子梅莉莎成了朋友,而且,在这个关系里,感到心虚的不是弗朗西斯,而是梅莉莎。
所有这些,是不可能产生于其他时代的,只能产生于这个社交媒体时代,是这个时代的“神经性耳鸣”。
好小说是时代的镜像,而萨莉·鲁尼用她那面仆人的破镜子,照出了一个时代的众生情感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