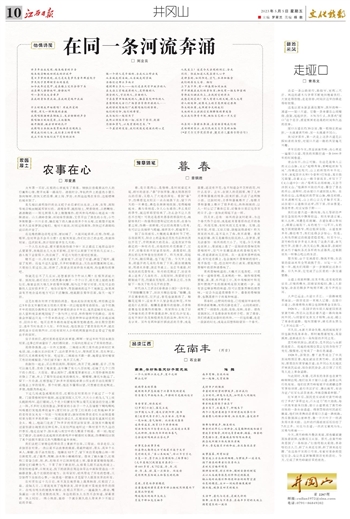□ 曾亮文
沿着一条山路前行,路较窄,宽两三尺许。两边的灌木与茅草不断地纠缠着我们。大家走得很慢,走走停停,时间在这里仿佛走得特别慢。
这是以前永新县通往厦坪、茨坪的唯一通道——垭口古道。它像一条青藤在山间缠绕、盘旋,起起伏伏。不知为什么,我喜欢“垭口”这个名字,感觉里面有沧桑的时间和久远的故事。
垭口古道长约35公里,像一根细长的扁担,一头挑着黄竹岭,另一头挑着井冈山。
我12岁那年,第一次走上这条古道是以探病者的身份,对垭口古道一路的风景毫无兴趣。
多年后的今天,我重返黄竹岭,决心再走一遍垭口古道,用我的双脚打通一条1000多年的时间巷道。
青山在目,白云可摘。左边是高耸入云的义山山脉,义山“起特秀耸,重嶂起伏如飞凤”,仿佛近在咫尺,山上的积雪终年不化。当年,黄庭坚在太和(今泰和)任知县,某日拨冗驱繁,沿着义山一路寻景而来,并写下了《义山道中》一诗:“莓苔石点雨痕斑,又忽寻诗到义山。”他满怀兴致往西走,攀登了著名的禾山,返程时,经由垭口古道回到太和。在我的右边,连绵起伏的罗霄山脉,峰峦相顾,草木清晰可见,山上的白云几乎触手可及。站在垭口古道极目远望,四下里,田亩葱茏,茶苗青青,村庄安卧于野……
我们沿着古道一路向南,鸟儿零碎的声音在急促的风中飘得很远。阳光穿透云雾,射入丛林,周遭色彩斑斓。古道依着山势而上,顺着山坳而下,有的地方一马平川,有的地方则坡陡路窄,两边壑深谷险。古道废弃多年,路径难寻,我们走得步步惊心。但是,人和鸟兽踩过的痕迹若隐若现。时至今日,黄竹岭仍有许多老人奔走于这条古道,春天挖竹笋、拾菌子,秋天采山果、摘油茶,农闲时砍来竹子编织各式各样的生活器具,过着跟祖先一样靠山吃山的生活。
想当初,由于交通滞后,物流不畅,生活里的盐油米布全凭肩挑手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挑夫们用脚一步一步地踩出这条小路。日久年深,它变成了山区里的一条交通要路。
古道上商旅相继,往来不绝,还有赴任的官员、打柴的樵夫、回娘家的媳妇,路上人影憧憧,杂沓的脚步声响彻不断,至今声犹在耳。
人声已远去,古道日月长。一段路被荒草淹没,一段历史却一直被人记着。在垭口古道上,弥漫着烽火烟尘也回响着金戈铁马。
1926年,一名22岁的年轻人秘密回到老家黄竹岭,然后从这里沿着古道一路向南奔向井冈,与同窗好友袁文才相聚,由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叫贺敏学,被毛泽东赞为“上井冈山第一”。
不久后,永新大革命失败,他的妹妹贺子珍也毅然投身革命。那时她剪着短发,英姿飒爽,逐渐成长为一朵绚丽的井冈之花。
黄竹岭居深山,滨溪谷,是井冈山与永新的连接点。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它的身份有了变化,慢慢地,它变成了一条红色通道。
1928年,郭荣良、曹工农等成立了中共东南特别区委,地址就设在黄竹岭。在此期间,郭荣良时常穿越古道,去井冈山关北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创办农民协会,还引领了王佐等人走上革命道路。
与此同时,朱德、毛泽东的身影也在黄竹岭频频出现,他们往来于垭口古道,迎着山风行色匆匆。他们在黄竹岭秘密开设湘赣边界军事培训班,进行苏区扩红、操兵练军,有诗为证:“红军生活苦连连,早练昼操星伴眠。”
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黄竹岭进行了多次“茅草过火,石头过刀”的大劫洗,每一次敌军前来扫荡,垭口古道便成了黄竹岭百姓的一条生命通道。得到警报的村民赶忙撤离,他们扶老携幼沿着垭口古道一路疾跑,然后散到深山密林里,像一片片叶子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扫荡前前后后历经了7次之多。村庄与古道,一次次丈量死与生,灾难与疼痛……
今天,黄竹岭格外整洁美丽,那些赣派建筑挂着新颜,安静而又从容。那天,在黄竹岭我看到了一条标语:“打铁唔怕火星烧,革命唔怕杀人刀,斩了头来还有颈,斩了颈来还有腰。”在这些平实的口号里,有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也让我重新触摸到历史的悲壮。今天,它成了黄竹岭最好看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