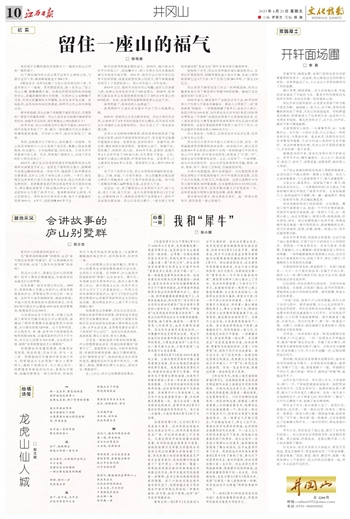□ 李 晃
早稻开花,晚稻出穗,老屋门前的九担谷田舒展着柔软的身子。远远地,我已察觉出它的欣喜与欢快。切莫得意过了头,小心来自大禾界的强风闪了你的蛮腰。
满山青翠,满园菜畦。在儿时的高山垄,早起的母亲遇见了早起的飞鸟。置身于叽叽喳喳的鸟鸣声中劳作,母亲总怀着一份幸福的心情。
我拉开碎花简易窗帘,从老屋木质窗户的方格子里往外瞅。扁桶坳上、豹子山、沙子岭,柔和的晨曦渐渐抬高了身姿,天色已然亮堂起来。村机耕道是安静的,即便是闯入了往来的乡亲,也没有让它变得有多喧闹。都是些老伙计了,点个头、问声好,继续不紧不慢地赶路。
我家菜园呈小坡状,一头紧靠禾坪,另一头挨着后山。在日复一日的岁月里,后山总是以一种慈祥的目光,与菜园对视。春去秋来,我想告诉它们有多默契多般配,告诉它们高山垄的时光有多静好。我这样琢磨的时候,母亲正打开菜园的篱笆门,手里拎着一篮子青菜。
做篱笆用的竹条,便来自身旁日夜守护的后山。春笋年年出,楠竹遍地生。山上山下,屋前屋后,修长了,结实了,成箕成篮,成箩成筐,刚好派上大用场。
为了防止家禽们特别是鸡进入菜园里搞破坏,必须在园子不挨山坡的一侧围上竹篱笆。母亲与父亲商量着说,马上就要放种子了,制几扇篱笆吧。
父亲点头,算是答应。回屋取了锯子、柴刀,转身径直走向后山。一支香烟的时间,好几根去了枝条的楠竹便应声倒在了屋前禾坪里。父亲估摸着尺寸,麻利地将竹子锯断,再一截一截地劈开,劈成一二指宽的竹条,然后编起篱笆来。
我向来敬仰劳动人民的智慧。比如篱笆。横向三排竹条韧劲十足,组成一个平行牢靠的框架。竖排的竹条依次紧挨着,前一条两头下压,后一条两头朝上,如此交替编入,棱角分明,线条流畅,好生团结、结实。再比如篱笆接口处的竹桩,须挑选楠竹靠近地面一端竹蔸的部分,削成侧锋的尖形,用力打进地里,稳固、经磨、耐腐。收成之后,来年还能再做贡献。
站在禾坪看菜园,菜园里生机勃勃,完全引领了高山垄的脚步,引领了这个半封闭式小山村的时序。菜园是一个神圣的存在。母亲弓着背、弯着腰,手握锄头,小心翼翼地,将那些掩在泥土里的生命唤醒。一株株睡眼蒙眬的菜苗破土而出,它们沿着与大地垂直的方向,站稳了身子,伸长了脖子,尽情吸收大自然的阳光雨露。
与菜园同样神圣的,便是稻田了。老屋门前就有,一大片一大片肥沃的良田,分属于不同人家。稻田与人一样,脾气秉性不同,处世方式不同,每季的收成自然也就各异。
记忆深处,我还是喜欢九担谷田。九担谷田离老屋最近。在窗前,在堂屋门槛边,在禾坪菜园里,便能闻见九担谷田的稻花清香。稻花稻穗,那是乡亲们的希望。
“双抢”来临,家家户户与时间赛跑,我们小孩子也参与其中。割禾速度慢,不小心还会伤到手,还是递禾把吧。我们在田野里来回奔跑,将一束束盘整齐的禾把迅速递到大人们手中。打谷机机声隆隆,大人们费力地踩着踏板。稻谷顺着滚子跳跃,兴奋无比。待它们玩累了,便一粒一粒落进户桶。田野上、田埂边,到处铺满了金黄的稻子,到处萦绕着丰收的喜悦。
禾坪里,一床床田封(老家一种用来晒稻谷的竹制垫子)早已就位。一担一担稻谷从田里挑回来,侧身“噗嗤”倒在田封里。竹耙子张牙舞爪,将带着草木清香的稻谷耙开、铺匀。太阳当空火辣辣的,母亲得戴上斗笠,半小时手动翻一次,让稻谷晒得充分均匀。
那时候,我家还没有修建水泥晒谷坪,铺田封的禾坪面积也不算大。必须抓紧时间翻谷、滤茅草,等晒干了这一批,紧接着晒下一批。等到晒它个四五天,随手抓起一把谷子,能咬出“咯嘣”响,就能过风车了。
过风车是个技术活。风车顶上有斗,斗里装稻谷,闸门一开,下面摇把就要滚动起来。摇把带动扇形的木片,力度必须均匀。饱满的稻谷落入箩筐,秕谷子从风车尾巴上飘出来。还有一些不是十分饱满的谷子,介于两者之间,我们称作“二藤谷”,从风车后槽落下来,装满了拿去喂鸡鸭。
稻谷过了风车,基本就能入仓了。装袋打包,鼓鼓的,沉沉的,一袋一袋扛回家,存放在二楼仓库。那便是一家老小的口粮。“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对于每一株水稻、每一粒粮食,父母亲都倾注了全部精力和汗水。一如对待我们,那也是他们的牵挂。
多年以后,我们走出了高山垄,离开了生养我们的故土。但父母亲还在菜园里劳作,还在稻田里忙碌。青山寂寂,炊烟袅袅。老屋沉默不语,三五小孩在墙根下嬉戏。
时光如水,我在未来的今日抬起头,看见天空高远,看见庄稼拔节,看见庭院安详。“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菜园、篱笆、稻田、晒谷坪,就像一枚枚充满乡土气息的针,把儿时的记忆缝在一起,串成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